自我有广延吗?
2015/6/3 哲学园

加小编个人微信号:iwish89 入群

作者简介:方向红,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
自我没有广延,已成定论,但胡塞尔晚年试图对这一定论发起挑战,因为他发现行为会“起效”,而“效用”会在自我中沉淀“堆积”起来,形成有“广度”、“深度”和“厚度”并延展着的存在,这些存在构成自我的习性、人格、禀赋或倾向并以此组成心灵的持守着自身特质的“本体”。经过进一步的论证,自我的这种广延被等同于胡塞尔晚年所探讨的“原对象”。从后者出发,耿宁在讨论阳明学派的道德意识时所提出来并企图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框架内加以解决的“寂静意识”的难题会迎刃而解,这种意识所包含的非对象性特征、静谧性的体验以及伴随性的情绪都得到了说明。
自我有广延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没有任何悬念。自笛卡尔把广延归于物体之后,自我或心灵没有广延性已经成为哲学的常识和共识。胡塞尔对此也是极为认同的。他在《观念Ⅱ》中表达了自己对笛卡尔的理解:“笛卡尔不无理由地把广延称为质料事物的本质属性。这种事物因此也直截了当地被称为物体性事物。与之对立的是灵魂的存在或精神的存在,这种存在在其精神性本身中没有任何广延,或者不如说,将广延合乎本质地排除在外。”①不仅如此,他还将这种理解提升至一种严格的原则性规定:“原则上说,在这一面(即心灵——译者注)没有任何东西在真正意义上、在我们所描述的广延的特定意义上是延展的”②。
由此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了结。然而,胡塞尔晚年在“C手稿”中却出人意料地把自我对其特性的固化和持守以及其自身的延展与物理对象的广延作了直接的类比:
作为内在的灵魂的个体形式,我们发现一种与客观绵延类似的东西,即在绵延中类似于过程的东西……在意识体验的持续的流动中,自我“持守”(verharrt)为在它之中所进行的体验的同一者并作为这种持守者获得了相对持存的特征,这些特征不是体验,而是在体验中“显现出来”的东西。作为具有这些特殊意义上的自我特征的自我,当它有时可靠地自我保持时,这个自我在其诸特征中持守自身、保持不变,或者,在其变化中持守自身。因此,在这种为它所特有的变化方式中,它也是持守者。这在形式上有点类似于物理性物体在其物理变化和不变中与时空广延(Extension)相关的持守性,不过,实际上,就其意义和类型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它(指心灵中的空间性——译者注)并不是某种第二类的、在复制性的映像意义上的空间性,它也不是同一个形式结构的个体形式。只是作为一个遥远的类比我们才在心灵之物中……拥有其每一次的延展(Ausbreitung)——空间性的广延正是在其中得以展现,而且我们拥有的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延展……③
很明显,胡塞尔并不是说,自我自身是或自我之中存在着某种三维的伸展之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话作这样的理解:如果我们把物理对象的广延性视为物理对象的不可入性意义上的坚固性以及坚持自身特质的持守性,视为该对象在空间上的延展,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自我具有广延性。
胡塞尔为什么要做如此重大的转变?他的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呢?下面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胡塞尔做这种转变的学理依据,④接着对胡塞尔的结论做进一步的引申,即把自我的广延解释为原对象,最后尝试用这种引申出来的观点解释耿宁关于“寂静意识”的难题。
众所周知,胡塞尔只是到了《逻辑研究》第二版时才明确承认了作为“必然的关系中心”⑤的纯粹自我的存在,并在《观念》时期把这个自我看作极点。这个极点是如此的纯粹,以至于我们必须把它与由它发出的行为严格地区分开来。自我总在肯定、否定、怀疑,在感知、回忆、期待,在吸引、排斥,在“做事”、“受苦”⑥,等等——这些都是自我发出的各种行为。这些行为,用胡塞尔的比喻来说,就像“射线”⑦一样,在进行的同时又回溯地汇聚于自我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自我就是自己所发出的那些行为。自我与自身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哪怕是把自我所有现实的和可能的行为都叠加起来,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自我。这种严格性不仅是出于对部分与整体的现象学关系的考量——整体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部分之和,更是时间性与非时间性的区分。胡塞尔说,沿着这些行为向源头返回,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我们发现了那个极,一个同一者,它自身是非时间的”⑧。具体而言,所有的行为连同其构造的对象都从未来流向现在和过去并最终沉入远方,与其他行为和对象融为一体,进入意识的虚无层面,而纯粹自我却始终驻留在现在,正如胡塞尔所言:“我们不要忘记:我的行为执行以及我的执行着的自我都已过去,可我并没有成为过去,我现在依然存在。”⑨
看来,自我是一个“空洞的”点、一个纯粹的极、一个非时间之物。这样的自我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进入其中,当然也谈不上任何广延性了。然而,胡塞尔晚年对行为的“效用”(Geltung)及其沉淀方式的发现为自我的研究打开了崭新的维度。
在《笛卡尔式的沉思和巴黎演讲》中,胡塞尔详细地介绍了他的这个重要发现:“这个中心化的自我并非空乏的同一极(正如任何对象都不会是空乏的极一样),相反,根据先验发生的规律,这个自我会随着每个从它发出的具有新的对象意义的行为而获得一个新的持恒的特性,例如,如果我在一个判断行为中第一次对一个存在(Sein)和如在(So-sein)做出决断,那么,这个转眼即逝的行为会消逝,但从现在起,我就是而且始终是那个如此地做出了决断的我,我是那个有了相关信念的自我。”⑩自我所做出的判断或决断行为已经成为过去,但自我因此而拥有的关于存在和如在的信念却沉淀到作为极点的自我之中,并在将来的可能的反复强化中成为“习性”(
)。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作为行为之效用的信念可以进入自我极并由此逐渐形成自我的习性!
一个认识行为发出又消失;一个认识对象出现又沉入记忆;一个实践行为做出来了,转眼成为过去;一个现实对象现在构造出来了,一段时间之后毁灭了,成了过去。对象不复存在了,可它以某种方式仍留在行为中,例如,我们可以通过记忆再现它,或者通过实践再造它。行为消逝了,它也以某种方式留在其效用里,例如,留在关于存在、勇气、公平和正义、善和美等信念之中,并最终凝结为习性、人格、气质、禀赋和倾向。正如对象完全不同于构造它的行为,效用也与留下它的行为有天壤之别。一次关于存在者的判断不同于存在信念,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的冲锋不等于拥有了勇敢的品格,对美的事物的欣赏不会立即带来审美趣味的转变——前者属于行为,后者归于效用;前者随时间流逝而不知所终,后者进入自我之中并在不断的累积中改变自我。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唯独行为的效用会进入自我之中呢?胡塞尔并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不过我们可以根据胡塞尔的意识哲学来尝试性地解释这一现象。我们把行为看作连接自我和对象的桥梁,在这里,胡塞尔的“射线”是个很好的比喻。行为,在以其肯定、否定、主动、被动、爱或恨等方式构造、遭遇对象的同时,也把这种构造或遭遇的后果传递给自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后果都是可传递的,事件或经历只能以对象的方式在相关的行为中存在,只有那些脱去了对象性特征而以纯粹主体性的方式存在的后果才能作为行为效用传递给自我,对自我产生影响并在自我中沉淀下来。举例来说,判断中的存在者,以及关于存在者的判断,是无法传递给自我的——因为前者是与自我相对立的对象,而后者正是自我发出的行为,能够传递回来的唯有关于这个存在者的存在信念;再譬如说,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这个事实以及关于这个事实的经验是无法传递的,但作为品格的勇气是可以进入自我的。行为的效用的传递之所以可以无障碍地进行,主要原因在于它与自我完全一致的主体性质。
胡塞尔的理论不仅可以解释行为的效用向自我传递的缘由,甚至通过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可以清晰地描述效用在自我之中的运行模态,揭示其向非清醒状态沉淀和累积的过程——胡塞尔本人正是这样做的。当行为把自身的效用传递给自我时,自我对它的把握是最清晰的,可是,如同原印象在滞留中不断地失实一样,自我对行为的效用的把握也会越来越模糊,最终消散进虚无。对效用来说,虚无是一种极限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行为的效用“不再起作用但仍被意识到,仍在把握之中”(11)。虽然效用变成了一种无效用,但正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效用在自我中已经被完完全全地抹去,它对自我的影响可以用零来指示。自我仍以某种方式拥有这种效用。胡塞尔通过一个假设告诉我们,在我们清醒的行为之下的是一个被遮蔽的王国,是一片沉淀下来的虽不再清醒但仍处于意识之中的领地,它是清醒行为的基础并贯穿其中——“设若这种保持、这种作为意向变样而或多或少远去的或被遮蔽的存在得到澄清,那么,我们在其中便会有一种沉淀,这种沉淀穿过整个清醒状态,当然(也)穿过整个清醒状态的综合系统。”(12)
既然行为的效用完全是自我性的,那么,根据自我相对于对象、身体和世界所具有的绝然性特征,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合理的推论:像自我一样,这些效用在自我与身体和世界分离之后依然存在,只不过换了一种存在方式。胡塞尔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只有当身体有机地存活着,一个人才存在;可是,我并不是我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在身体中起作用。如果身体瓦解,我就不可能起作用了,对任何从这种可理解的起作用出发把我看作共在者的人来说,我都不存在了。没有了身体,我就不可能对世界上的事物产生作用,也不可能进行告知、言说或书写,等等;可是,我越过了身体的界限……也许……我的人的习性、我的信念、效用,其中也包括对我有效的世界本身……都被锁闭在我之内,无法被激活,以便进一步进入世界的活动中。”(13)显然,在身体的界限之外,在世界的活动之先,不仅自我存在,而且属我的效用也存在,只不过其存在方式是潜在的、锁闭性的,或者说,是尚未激活的沉淀物。
这种沉淀物就是自我的习性、人格、禀赋或倾向,它们组成灵魂的延展着的“本体”(Substanz)(14)。它们本身既不是行为,也不是体验,而是将来可以通过行为或体验“显现出来”的东西。(15)在未来的自身显现过程中,它们在一定阶段上总是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展现着某种类似于在物理对象的不可入性意义上的坚固性以及坚持自身特质的持守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心灵的“广延”——我们似乎看到,这些与行为相关但本身不是行为的东西在自我中沉淀“堆积”起来,形成了有“广度”、“深度”和“厚度”并延展着的存在。
在确定了自我的广延性之后,我们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这种广延究竟是什么?据笔者的有限阅读,胡塞尔既没有正面地提出这一问题,也没有做出即便是间接的回答。下面我打算依据胡塞尔的思路,提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胡塞尔晚年分别从自我和质素出发,通过“现象学的考古学”方法,回溯地建立起“原自我”和“原非我”这两个概念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原自我既主动地触发原非我,又被动地受到原非我的触发,但它们并非两个截然不同且相互分离的存在者,而是一物之两面,它们只有在抽象的反思中才能被区分开来。(16)
这样建立起来的自我的原初模式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它无法解释原自我在同原非我触发和被触发的过程中所构造的作为自我的主观成就的意向对象为什么能够切中体验并获得了客观性。我们知道,这两个“我”尽管不是两个实体,但毕竟分属触发或被触发行为的两侧,如果它们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基础,它们所构造的对象要么偏向主观,要么偏向客观,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
其实,这种模式还有一个缺陷。用意向性结构来描述原自我和原非我的触发性关系,我们会发现,作为原素的原非我进入到体验流之中,而身为极点的原自我则带着自己的兴趣开始其构造活动,但自我的广延性没有发挥任何特殊的作用。在意向性结构中,自我的广延似乎没有任何位置。
原自我的广延部分在“原活当下”的构造过程中有没有起到作用呢?如果有,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让我们利用意向性结构先行做出一个猜测。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意向性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包含实项材料和意识行为于自身的意向活动、具有确然性的超越的意向对象以及具有绝然性的超越的自我。在“原活当下”还未被构造出来之前,原自我扮演了构造后的超越性自我的角色,原非我处于实项材料的地位,这时意向对象还未出现,能不能就此做出大胆的设定,自我的广延这时恰恰以意向对象的身份出现?我们能不能由此推断,自我的广延就是原对象?让我们重温一下前文所引的胡塞尔关于自我的广延性的论述:
在意识体验的持续的流动中,自我“持守”为在它之中所进行的体验的同一者并作为这种持守者获得了相对持存的特征,这些特征不是体验,而是在体验中“显现出来”的东西。
从意向结构来看,在体验中呈现出来的东西只有两种:自我和对象。自我作为原自我始终维持着它的“持守”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广延作为“持守的特性”通过体验而自身显现。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广延正是意向结构中的原对象。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自我的广延作为沉淀物本身就是自我的组成部分,把这个组成部分当作自我的第一个对象,这难道不是一种自身循环?这确实是一种自身内的循环,一种费希特意义上的“自我设定自身”的循环,可是,若没有这种循环,会出现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原自我和原非我的统一性以及意识的一个核心特征(自身意识)都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下面让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
原自我首先分裂为作为极点的自我和作为“对象”的自我(17),前者意识到后者并把后者当作属己的对象收入眼帘。这时,触发性的原素流入进来,充实了后者,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首先是形式对象,接着是含有实事内容的对象被构造出来。于是,原自我清醒过来,成为自我,它朝向的是它刚刚构造出来的对象,而此前的原对象退到对象的背后,成为一同被意识到的背景。这种作为背景的非对象性的被意识到,正是胡塞尔所谓的自身意识。
这是原自我的自身循环的一个积极的结果。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如何导致原自我和原非我的统一性的。如果像胡塞尔所认为的那样,原自我和原非我并不是两物,而是一物之两面,那么这“一物”是什么?看来它非作为广延的原对象莫属,只有它同时与其“两面”发生关系。我们看到:一方面,它发自自我,是自我的各种行为和“射线”以效用形式发生的沉淀;另一方面,它直接关联到事物或对象,事物或对象自身的杂多性、历史性、阻抗程度等也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自我的决定和取舍并因此参与到效用的形成之中,而且,在随后出现的新的构造活动中,这种作为效用已经沉淀下来的广延也决定和取舍着原素参与触发和充实的可能性和程度。正是由于它一身兼两任,才使得原自我和原非我不至于蕴含二元论之忧。
带着这样的理论结论,让我们来考察一桩关于“寂静意识”的公案。这是耿宁在《中国哲学向胡塞尔现象学之三问》一文中讨论阳明学派的道德意识时所提出来并试图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框架内加以解决的难题。
根据耿宁的理解(18),王阳明的弟子们曾在道德意识的意向性本质上进行过一场大论战。以钱德洪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意识(知)必定有其对象,“人情事物”正是这样的对象,脱离了这些对象的“感应”,意识(知)本身便不存在了。这一派在道德实践上主张,我们只有在行为中通过意志弘扬善的意向、拒绝恶的意向才能达到自发行善的结果。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艰苦的努力。以聂豹和罗洪先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反对这种通过意志努力践行道德意识的路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人为的而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他们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不再对每一个“人情事物”进行褒贬,然后做出去恶扬善的道德抉择,而是走到意向的“发用”之前,走到一切道德事件成为对象之前,直接面向心灵或精神的寂静本体。他们相信,当人“沉浸”在对寂静本体的冥想之中后,便既不需要区分道德上的善恶,也不需要特别的意志上的努力,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意向“发用”会自发地且清晰地符合善的要求。
耿宁利用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对这种“寂静意识”做了深入的分析,其思路大致如下(19):寂静意识是不是胡塞尔所谓的“空洞的视域意向性”呢?初看起来似乎是的。寂静的、冥思的意识是对主体潜能的意识,这一意识当然是空乏无物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种意识就是胡塞尔的“空洞的视域意向性”。可是问题在于,这一意识仍然必须与冥思者当时的“直接当下”相关联。如果失去了这种关联,冥思者可能会进入睡眠或做梦之中,在这种状态下他是没有能力通过悬置其梦境而变得清醒起来的。因此,与现实当下的关联对于寂静意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可这样一来,它就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视域意识了,因为视域意识总是依附于某个对象,作为某个对象的背景意识而存在,我们当然不可能把寂静意识看作是“直接当下”的背景意识。
有没有可能将寂静意识理解为胡塞尔在反思儿童意识发生时所提出的“原开端的视域”或“原视域”呢?这种视域是意向敞开之前的潜在状态,是意向对象得以构成的基础,寂静意识朝向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吗?根据王阳明的一位弟子欧阳德的理解,寂静意识无需五官和理智的作用,它“虚融澹泊”地专注于一个尚未分化的“东西”。显然,胡塞尔的“原视域”中虽然没有对象,但对象已经隐含在意向之中并即将从中构造而出,且将为儿童所感知;而欧阳德的寂静意识“是一种并不朝向某个从万物中分化出来的对象的精神状态”(20),就是说,这种意识不以对象的出现为目的,即使对象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因此,这两种意识状态是完全不同的。经过细腻的比较和分析之后,耿宁最后得出结论:“意向性的概念难以应用到这一‘清晰的意识’上。”(21)
耿宁的结论是否定性的。可是,如果道德意识仍然是意识的一种形式,那么意向性就必然是它的结构。现在我们不妨从作为自我之广延的原对象的视角出发来探讨意向性概念在寂静意识上的应用的可能性。
我们设定,寂静意识是朝向原对象的意识。当然,原对象不是现实的对象,而是属我的、具有同一性和持守性的、类似于广延的东西,换言之,它就是沉淀下来的信念、人格、禀赋和倾向。因此,寂静意识对原对象的注视不是对自身之外的某物的注视,而是自我对自身的注视。这样的设定是否可行?这种自我注视如何操作?它在日常的对象意识的进行中有无源头?耿宁曾经中肯地指出:“如果能够追溯这种寂静意识的出现到其日常意向的对象意识中的起源,可能可以继续一种现象学的分析。因为冥思的意识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艰难努力和渐进过程的结果。”(22)
我们知道,胡塞尔的现象学悬置方法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其源头在我们的自然态度中。寂静意识也是如此。在日常意向中,我们不仅可以轻易地从对对象的意识转向对与其相关的行为的意识,例如,从感知的对象转向对对象的感知分析,从所爱的人转向对这种爱的肯定或怀疑,从一个美的事物转向对该事物的审美描述,等等;我们还可以把目光从每次的行为转向该次行为的效用,例如,从感知分析转向对存在的惊奇,从对爱的肯定或怀疑转向爱的喜悦或绝望,从审美描述转向审美愉悦,等等。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当然这需要一点“艰难努力”,摆脱自然态度,把我们自己置身于超越论的还原之中,将目光聚焦在沉淀下来的作为总体的行为效用上,这时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首先会发现,曾经如此熟悉的对象感消失了。在我们的目光转向每一次的行为及其效用时,行为和效用成了对象,尽管这是与该行为或效用所关涉的对象完全不同的对象,但我毕竟可以在一种“我思故我在”的直接性中把握到它:我感知,我知道我在感知和惊奇;我爱,我知道我在爱,我在喜悦和绝望;我审美,我知道我在审美和愉悦,如此等等。但当我们的目光转向原对象时,由于经过了本质还原和超越论的还原,个别的对象以及与它相应的行为及其所引发的效用都被悬置了,我们处于一种奇特的两难境地。若说此时没有对象,我偏偏可以有“清晰的”意识,信念、人格等的确是真实地存在于我之中的东西;若说有对象,我却无法如面对感性对象那样间接地或如面对自我的各种行为及其每一次的效用那样直接地把握它。
接着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意识,一种不存在任何对话或交流的可能性的意识。如果说对象性意识是一种“喧嚣的”、生机勃勃的意识,那么,在剔除了对象和行为之后,我对处于潜在和锁闭之中的“本体”的意识就是一种寂静的意识,一种“虚融澹泊”的意识。
最后,我们会发现,这种寂静的意识会伴随着强烈的“情绪”——心灵体验。我们知道,原对象本来是等待原素的充实的,可当我们对原素做了悬置并把原对象带入眼帘之后,期待充实的原对象反而充实了另一个“对象”,一个新的“对象”,或者说,一个新的“对象”通过原对象而被自身给予了。这个新的“对象”就是耿宁所甄别的王阳明晚期提出的“良知”(23)。就像在海德格尔那里,虚无是挂在存在上的帐幔一样,原对象似乎也是“良知”的外衣。在这种“良知”的映照下,在自我中所沉淀下来的信念、人格、禀赋和倾向,其是非善恶暴露无遗,静观的自我会情不自禁地像欧阳德那样产生“喜乐”感;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其他情绪,如海德格尔的“畏”、帕斯卡尔的“无聊”、陈子昂的“怆然”,等等。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胡塞尔原来意义上的意向性结构,确如耿宁所言,难以应用到对“寂静意识”的分析之上。不过,在引入原对象概念之后,这种意识所包含的非对象性特征、静谧的体验以及伴随的情绪都得到了说明,这种说明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对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乃至现象学本身的理解——恰如耿宁所指出的那样:“在现象学面前有一个广阔而至此为止极少得到探索的研究领域,它也许会以一种全新的可能和光明,向我们揭示出人类的意识、人类的精神。”(24)
注释:
①E.Husserl,Ideen zu einer rein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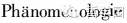
und 
Philosophie,Zweites Buch,Husserliana,Band 4,hrsg.von Marley Biemel,Haag:Martinus Nijhoff,1952,S.28-29.强调形式为原作者所加。
②Ibid.,S.33.强调形式为原作者所加。
③E.Husserl,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1929-1934):Die C-Manuskripte,Husserliana,Materialien,Band 8,hrsg.von Dieter Lohmar,Dordrecht:Springer,2006,S.387.
④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第一节中所做的这种梳理是极为简略的,更详尽的说明请参见拙文:《自我的本己性质及其发展阶段——一个来自胡塞尔时间现象学手稿的视角》,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⑤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页,注1。
⑥E.Husserl,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S.188.
⑦Ibid.
⑧E.Husserl,Die Bernauer Manuskripte über das Zeitbewusstsein(1917-1918),hrsg.von Rudolf Bernet und Dieter Lohmar,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S.278.
⑨E.Husserl,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S.201.
⑩译文转引自倪梁康:《“自我”发生的三个阶段:对胡塞尔1920年前后所撰三篇文字的重新解读》,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11期;又见E.Husserl,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Husserliana,Band 1,hrsg.von S.Strasser,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1,S.100-101。强调形式为原作者所加。
(11)E.Husserl,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S.313.
(12)E.Husserl,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S.376.括号内的文字为引者所加。
(13)Ibid.,S.442-443.
(14)胡塞尔曾明确地指出:“灵魂的‘本体’(Substanz)的本质形式是人格。”(E.Husserl,Z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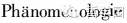
der 
,dritter Teil,Husserliana,Band 15,hrsg.von I.Kern,Haag:Martinus Nijhoff,1973,S.342)
(15)正是由于它的将来维度,有学者与胡塞尔一起把习性归结为“潜能性”或“可能性”的一种。参见Werner Bergmann & Gisbert Hoffmann,,,
als 
:Zur Konkretisierung des Ich bei Husserl“,in Husserl Studies,1984(1),S.298。
(16)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拙文:《宛如“呼吸、睡眠中的呼吸”——胡塞尔对Hyle之谜的时间现象学阐释》,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7)当然,正如胡塞尔已经强调过的那样,自我的广延性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对象,就是说,它既不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定位,也不是观念意义上的存在,它仅仅具有延展性和持守的自身一致性。
(18)参见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倪梁康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66-467页。(下引该书,简称为《心的现象》)
(19)同上书,第469-471页。
(20)同上书,第471页。
(21)参见耿宁:《心的现象》,第471页。
(22)同上。
(23)按耿宁的理解,王阳明晚期的“良知”概念“从根本上说不是意念,也不是意念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而是在每个意念中的内在的意识,包括对善与恶的意念的意识,是自己对自己的追求和行为的道德上的善和恶的直接的‘知’或‘良心’”(《心的现象》,第182页)。
(24)同上书,第471-472页。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哲学园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