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不应把国学研究当成向西方宣战的武器 | 检书26
2016/4/12 哲学园
作者: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
精彩观点
在今天的国学研究中,把国学研究当作弘扬民族精神的工具,当成向西方宣战的武器,当成满足私人心理需要的手段,也许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今天我们发现在东亚许多国家,科学研究不是为了满足人性的好奇心或追求普遍真理,而主要是为了给民族争光,这才是科学精神丧失的主要根源。
对于中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来说,如何以健康、理性的态度看待历史,开展正确的历史教育,是决定千千万万人走出民族主义陷阱、摆脱其消极影响的关键之一。
以下为正文:
一、民族主义下的国学研究:总想证明中华文化举世无双
如果说文化无意识是指一个文化中特有的、在无意识中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或观念,那么可以说,东亚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形成后,作为一种糅合了家族主义和团体主义的无意识,操纵了无数人的神经。
从这个角度说,东亚民族主义却又像是土生土长的。至少,由于它在东亚文化土壤中找到了稳固的根基,已变得非常强大、不可一世。

东亚民族主义并不愿意退场
东亚民族主义中的“文化无意识”,就是人们在追求民族利益的时候,未必十分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支配自己神经的思想观念。
比如,一个人爱国、希望自己的祖国富强,本来是十分正常、合理的。但是如果他在学术研究中以证明自己的祖国无比伟大、自己的文化辉煌灿烂为唯一兴趣,必然难以客观面对那些和这一目标不一致的事实,不可能严格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则和规范,从而极容易败坏学风、破坏学统。
文化团体主义者的心理是,集体(“祖国”)越强大,我个人的心理越有安全感。你以为他们真的爱国吗?在他们的心中,所谓国家利益、民族需要,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幌子罢了。隐藏在国家利益和民族需要背后的,其实只是某种难以启齿的个人心理安全需要而已。
多年来,民族主义正是以上述方式在中国学术界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强大作用,在国学界尤其如此。在今天的国学研究中,把国学研究当作弘扬民族精神的工具,当成向西方宣战的武器,当成满足私人心理需要的手段,也许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如今的国学研究已经被当作弘扬民族精神的工具
喊着“天人合一”口号的学者,未必真追求天人合一,而是要证明中国文化伟大;宣扬儒学的学人,未必真践履儒学价值,而是要证明中国模式优越。宣称仁义,未必就有仁义,而是在寻求身份认同。
我们看到一些大谈传统文化的学者,一遇到国际争端,马上想到诉诸武力,或者韬光养晦以便将来诉诸武力;有些力倡和而不同的学人,一遇到西方威胁,立即叫骂不已,毫无和合精神;有的以儒学自居的人士,一听到批评中国,顿时恼羞成怒,完全丧失了理性。

亨廷顿和他的“文明冲突论”
比如,有些人到处批判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批判基督教文明侵略性强,总之西方人不如中国人高明,中国文化向来就是主张“和而不同”的。但是与此同时,恰恰也是这些人,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的使命就是要与西方文化争夺地盘。且不说其对亨廷顿的原意误解甚深,更重要的是自己才是从完全对立的立场来理解西方文化,故而宣扬中西文化非此即彼的争夺战或阵地战。
造成这一状况的真实原因只有一个:论者自己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和合之道,唯一感兴趣的不过是证明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而已。

作者: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
又比如,笔者曾指出,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黑格尔可算从哲学上系统地证明了“天人合一”的三位伟大哲学家。许多国学研究者热衷于宣扬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多么伟大。但这三位哲学家对于“天人合一”的论证,从思辨性上远胜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了。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黑格尔(从左至右)
如果是真心宣扬“天人合一”的话,为什么不提及这三位哲学家呢?难道喜欢“天人合一”是假,要证明中国文化伟大是真?
总是想证明中国文化举世无双,总是不接受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总是喋喋不休地责备他人,其实只是要发泄一种情绪,寻找到一种慰藉,不管这种情绪或慰藉是健康的还是变态的。
二、儒学研究者是如何成为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的?
为什么国学研究会变成这种状态呢?因为,今天的儒学研究者往往不再有基于人性永恒需要的伟大信念,不再有为全人类立法?或开太平的宏伟自信,于是他们只能堕入民族或国家的集体想象中,成了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
本来,在公民民族主义或自由民族主义看来,没有国界的个人自由与有国界的民族空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民族国家被理解为公民的契约,个人价值与国家需要分而置之。民族主义对集体利益的追求和捍卫,只能在有限的、不侵犯个人自由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但在中国或东亚则不同,由于文化团体主义影响,个人价值历来与集体需要合而论之,不能分置。于是集体利益变得无限神圣,可以打着国家或民族利益的旗号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人自由、占领一切领域。
在学术领域中,这就表现为:无视学术规则,没有学术规范,一味地要证明中国思想高明,把学术这一人类本来崇高的事业变得低俗、无趣。如此下去,如何能走出国门,赢得世人的尊重?还是反而让外人更加瞧不起?
例如,有的学者动不动说,西方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思想,真正理解中国思想的是我们自己。他们确实容易从其著作中找到一些证据,证明对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不够准确、到位。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他的清史研究十分有名。
然而事实上,即使是同样的经典和材料,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不能以中国人所习惯的那套训练作为所有人研究国学的共同基础。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汉学家们有自己的一整套相当成熟、健全的研究范式。在对后者缺乏入乎其内的了解的基础上,仅仅由于其对中国经典的了解程度不如我们,就急于下判断,否定西方汉学研究的意义,是十分可笑的。
事实上,如能掌握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范式,就会发现其不容置疑的意义,认识到西方汉学研究或儒学研究有中国国内同类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其在很多重要领域的成就早已超过国内同行。
相比之下,一些中国学者由于长期沉浸在一些大而无当的课题上,缺乏研究规范上的成熟和严谨,学术成果总体质量很差。其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就是对国外同行的成果了解较少,低水平重复甚多,往往对某一问题没有系统、完整、全面的前期掌握就急于下笔。

1648年,欧洲国家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本来,在西方,民族国家由于是自发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人们认识到民族国家是作为帝国的替代而形成,所以民族主义本来与传统意义上、以征服和统治天下为宗旨的帝国主义是相反而对立的。
但是在中国和东亚,由于民族主义完全是挤压出来的,出于挤压的反弹,它似乎带有天生的复仇情结。这一情结进入国学研究中,使学者们在精神生命深处不甘心与其他民族相安无事;古代的辉煌和近世的屈辱,被鄙视的伤痛和被排挤的压抑,各种丰富复杂的情感合在一起,终究要找一个发泄的窗口。所以他们的民族主义是带有攻击性的,与西方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殊途同归了。
然而,一味重视国家需要,忽视文明价值,不利于找到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把国家需要凌驾于文明需要之上,决不能保障社会生活的长治久安。狭隘民族主义的形成固然与近代中国备受欺压的特殊命运有关,但从深层上是由于一些儒学研究者无意识中把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与自己血液里深藏的文化团体主义因子相结合的结果;试图塑造一个统一、强大的新型国族当然没错,但把王道主义的文明理想置于次要位置,绝非儒家观点。
在一些中国学人心中,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只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走向一个世界性帝国的,唯此方能找回昔日的辉煌。所以,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民族主义变得非驴非马了,因为它的终极目的似乎是要摆脱民族、统治世界。它确实追求民族和国家利益,但骨子里是要建立帝国。因而,它骨子里是由传统的家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文化团体主义所衍生出来的帝国主义思维。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地位的提升,恰恰也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地区对国人的修养、胸怀、心态密切关注的时候。一个令人忧心的事实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国学学者缺乏应有的心胸和气度,不能真正吸纳各国的优秀方法和成果,不能包容异见和批评;喜欢自吹自擂,用中国文化引领世界;乐于自我标榜,用中国思想拯救人类。他们动辄建立学派、提出流派,创说法以代替研究,喊口号以引领潮流。凡此种种,给外人预期以巨大落差,也和这样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形象不相称。
三、必须彻底清理民族主义遗产
通过分析儒学/国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比如,民族主义今后该往何处去?尤其在中国和东亚,该如何处理民族主义问题?
首先应该承认,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18世纪以来全世界范围内伴随民族国家兴起的全球浪潮的一部分,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迫于应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二战以来的全球化浪潮而形成的。
正因如此,只要民族国家没有消亡,并且事实上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人类结成政治共同体最主要而有效的方式,民族主义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等所开创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都没有也不会过时。
然而,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它的负面因素缺乏清醒认识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西方,民族主义曾经导致殖民运动和帝国主义,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东亚,民族主义通过与东亚自身的文化土壤相结合之后,形成了东亚特有的民族主义思潮,其负面效应同样不容小视。为了彻底清理民族主义遗产,我们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认清民族主义的真面目,了解它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反对民族主义,只是要反对那种极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于极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尤其警惕它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它好比是一个幽灵,能轻而易举地钻进任何人的体内,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受其驱使。
从这个角度说,儒学特别是国学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极易成为民族主义的寄生之所。在儒学/国学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中,民族主义是里,儒学/国学只是表。儒学/国学被民族主义利用、扭曲,当事人被民族主义主宰、奴役,却浑然不知、心甘情愿。
当然,民族主义这个幽灵也能钻进其他一切领域,发挥无所不在的作用。比如科学、技术、市场、宗教、学术这些行业,本来是超国界、超民族的,但它们也可能变成为民族主义服务的工具,从而逐渐掏空行业的价值,毁坏行业的规则。比如一项研究表明,二战以后日本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远超过德、法等欧洲强国。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远少于德国或法国。

东亚更倾向于把科学研究当作解决实用需要的工具,而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
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倾向于把科学研究当作解决实用需要的工具,而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今天我们发现在东亚许多国家,科学研究不是为了满足人性的好奇心或追求普遍真理,而主要是为了给民族争光,这才是科学精神丧失的主要根源。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领域。
第二,必须反省我们的历史观和历史教育模式。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伤性记忆是人格扭曲的重要根源。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不能从其不幸的创伤经历中走出,就难以有健康的心态和健全的人格。在这种情况下,受伤者由于心理安全感得不到保障,容易无限夸大威胁的存在,通过把敌人丑化、妖魔化和绝对化,发泄自己在情绪上的不安。

弗洛伊德
对于中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来说,如何以健康、理性的态度看待历史,开展正确的历史教育,是决定千千万万人走出民族主义陷阱、摆脱其消极影响的关键之一。我们不能让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永远生活在历史的伤痛中,让他们从小埋下仇恨的种子。我们应当培养下一代对其他民族、包括曾经伤害过我们的民族及其人民的包容和爱心。
一百多年来中国所遭受的侵略和殖民,是16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殖民运动的一部分,并非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或民族而来。而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兴起后,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拓市场、追逐利润所致。我们不应该由过去的遭遇上升到认为西方民族“本质上”就是侵略性的。
应该认识到,在过去几千年历史上,中国人也曾经对周边许多人,包括许多族群和小国进行过无数侵略或欺压。今天华夏后裔的生活空间从原来黄河中下游的狭小空间,扩展到近千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并不完全是以和平方式得来的,其中也包括许多战争和杀戮。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秦始皇以来对江南大片区域的强行扩张,蒙古人对中国及其周边巨大空间的武力占领,满人对汉、蒙、回、维、藏等在内几乎所有族群的军事征服,等等。凡是研究过春秋战国史的都知道,当时中原国家如晋、齐、楚、秦、鲁等国,对周边很多少数族群进行过无数次毁灭性打击。通过甲骨文我们也知道,三代以来中国周边的许多族群,包括所谓鬼方、土方、羌方、虎方、人方、莱夷、九夷、犬戎之类,早已消失在历史云烟里,被汉族消灭或同化了。
假如有人今天以这些历史故事为由,上升到“本质”的高度,说中华民族“从本性上”就好侵略,像今日许多韩国人、越南人所认为的那样,你能接受吗?
当我们为过去百年来的民族屈辱而耿耿于怀时,可曾想过我们的祖先也曾经欺压或侵略过其他人;当我们为近代以来丧失的土地而愤愤不平时,可曾想过我们也曾在征战中得到大片原不属于我们的土地?
如果把过去几千年人类历史综合起来看,华夏族群未像无数其他族群那样被消灭,而是像滚雪球一样地不断发展,今日生存空间更是全球屈指可数,相比之下我们还算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幸运者之一吧?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知足呢?假如我们希望别人原谅我们祖先的侵略和欺压,我们是否也应对那些侵略和欺压过我们的民族多一份平常心?
第三,原教旨式的中国文化本质论或西方文化本质主义都是完全错误的。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不同文化的交融史。从传承关系上看,今天考古学家已经日益发现中华文明有多个源头、并不单一,这难道不是对华夏文明本质论的一种驳斥吗?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存在。
诚然,今天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必要。但是如果以一种近乎图腾崇拜的方式来论证一种儒教与政体合一,或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及其再生,仿佛有一种中华文明的“原型”(prototype)等着我们去找回似的,这是从一开始就将中华文明自绝于其他文明,何况原型意义上的中华文明本来就不曾存在。儒家的政道或治道是不是一定比西方的或人类其他文化中的政道或治道优越,最好不要言之过早;在涉及文明优劣问题上,最好多给外人留下谦卑而不是自负、包容而不是排外的印象。
第四,如果说今天儒学乃至整个国学研究被民族主义绑架了,这不是由于儒学或国学复兴错了,而是由于复兴的方式错了,因为学者失去了对于生命尊严与价值的崇高信仰,失去了对于普世文明的伟大理想。
虽然儒家从爱有差等的逻辑出发,和民族主义非不相容,甚至一定会支持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但是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是天下主义的,必定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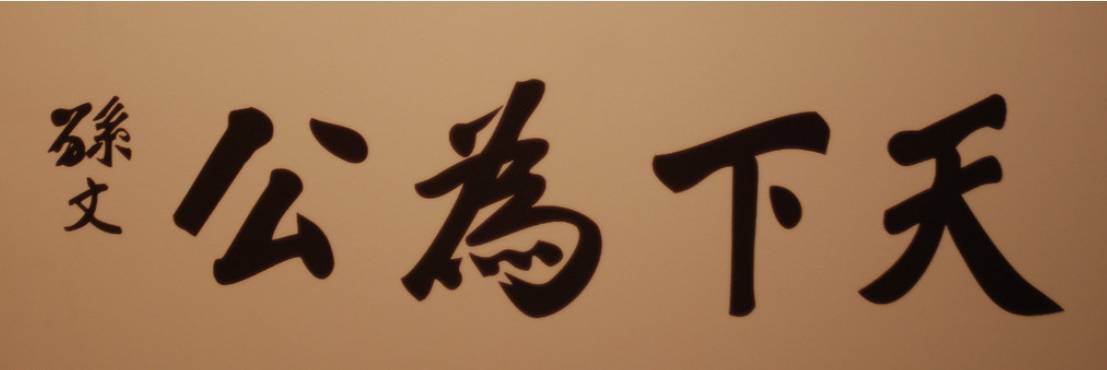
孙文题写的“天下为公”
因此,要想真正走出民族主义陷阱,必须回到儒学的天下主义精神,即对普遍人性和普世文明的信念。只有从抽象人性的不朽价值和普世文明的伟大理想这两个基点出发,才能真正接续儒家命脉,光大儒学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才能为现代文明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因此,今天怀抱复兴国学、传承儒学使命的学人们,应当认真地考虑清楚,如何用合乎人性的逻辑、合乎文明的规则来阐明你们的观点。
弘扬传统文化固然不错,但在学术研究中,一定要严格按照全世界共同接受的学术规则来论证,才能被世人接受;建构儒家治道或政体理论诚然很好,但最好充分理解人类各重要制度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条件及其限制,才不至于让人觉得孤芳自赏、夜郎自大;欣赏“三纲五常”当然可以,但只有从社会秩序的普遍原理出发,才真正有说服力(笔者本人是这么做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要想彻底清除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意识形态、教育、媒体、行业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国际交流等因素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需要所有这些领域联合起来、多管齐下。(作者:方朝晖;编辑:李大白、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杂志2016年第2期,本篇为全文第二、三部分,腾讯思享会受权发布,发布时有删改,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长按下方二维码,识别关注。)

栏目简介

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读书在今天可以变得更便利,但不会变得更轻松。为增广智识的读书,不妨给自己加一点点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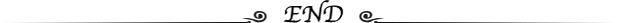
腾讯思享会(ThinkerBig)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哲学园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